| 个人简介 |
| 艺术家官网二维码 |

|
| 扫描二维码 关注艺术家 |
| 电子画册 |
| 作品润格 |
| 联系方式 |

一、
仲秋之日,朋友发来几幅画作。
信手打开,秋风顿至,萧索肃杀,一万点蹄声携带草原霜雪之冷冽,月色之清寒,羌笛之凄寒,地域之空袤,席卷而至,势不可挡。马!蒙古马!一万匹蒙古马纵横风中,扬鬃曳尾,奋起四蹄,或仰天嘶鸣,或纵身腾跃,或侧身超赶,或扬蹄追风,不驯不羁,大开大合,如洪流泄地,如金光穿云,如万箭过空,横空出世,骇俗惊世,不可一世!

包布和,内蒙古通辽扎鲁特旗人也,生于草原,长于草原;家如穹庐,天似穹庐;草原有我,我有草原。提缰跃马,啸傲春风草场;对月扬鞭,高歌秋月如诗。蒙古人包布和以马为梦,但上马背,四蹄生风,人马化龙,乃不知何者为人,何者为马?人并马跃,疾风劲草,云天变幻,繁花碧湖瞬息虚化,千里时空旦夕转换,因此吞吐辽阔,始有胸襟气魄。而后学画,离乡南北奔驰,心中结界千里云天万里关山,年华遭逢一并化为给养,心中苍茫意象茫茫荡荡,心门打开,万马来朝,或煊赫浩荡,或衔枚疾走,一时风雨交加,一时涕泪滂沱。
风起于青萍之末,包布和的绘画由“意”而起。其意则如何?抒情,回忆,疼痛,悲伤,悲欣交集。乡愁,回不去的童年与故乡,留不住的人事,挽不回的感情,诸多美好而易逝,大风一样席卷过他渐渐苍凉的人生。蒙古人的豪情,蒙古马的不羁,催生了他必然舍去形似而直奔意象、神似的道路。那狂放的激情,岂是细笔慢描所能表达?那烟雨苍茫,岂是“气韵”所能涵盖?必以我意摄取其神,必以我笔重塑时空,必于方寸之间,见无穷之意。必须狂放,必须淋漓尽致,必须饱满酣畅,于是万千物象争相纷至沓来,入于其心,凝于其笔,现于其墨,始有新气象,新天地,新章法。

非也。

二、
中国画论多崇尚“气”说。“气”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亦为中国文化品格和文化趣味之重要特点和论点。“气”使得中国文化崇尚得其神而略其形,如中医之筋络,如绘画之写意。然则,何者为“气”?并无确切答案。
《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是“太初”,“太初者,气之始也”;孟子的“浩然之气”是气,是磅礴之气,自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也是气,是柔靡之气。由质朴天真到气势浑然刚健,再到“去势”化,文化中的刚性在逐渐消解,阴柔成为中国艺术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文学上,则相对应于《诗经》、《诸子百家》秦汉文章和宋词元曲——便是有唐一代,盛唐、中唐、晚唐,艺术上亦迥然有别,诚如胡应麟所言:“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晓月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今古,而盛中晚界限堑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表现在绘画上,则对应于原始壁画、魏晋汉唐宗教绘画与山水画、宋元明清的文人画。

“气韵”是南齐谢赫提出来的,他将“气韵”列为六法第一,“气韵”成为评判作品的主要标准,几乎独占了“气”说母集的全部,使得众人皆知“气韵”而不知“气势”,“气势”日薄西山。然而,“韵”到底是什么?陈传席先生考为首用于魏晋时代的音乐和人物品藻,一种只可意会的雅致。难以言说的“韵”,甚合文士们审美品位。掌握了话语权的文士们,更是将“韵”进行概括、提炼、神话,进而倡导,玩味,墨戏,中国绘画整体滑向“趣味化”,“时代精神不在马背,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鲜活泼辣的生活,山川形胜的宏大,大地上的美学存在,逐渐让位于“心中的山水”,正如龚自珍叹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汉唐气象逐渐消亡。“气势”逐渐衰颓,中国画丧失了宏大浩然的一面。

诚然,气韵确然合乎中国画,然玩味、趣味终究会割裂或淡化生活、现实对艺术的影响和加持,纯艺术必然会走向小众和式微,其格局必然会缩小,走向孤僻、怪异、自以为是,满身的遗老气息。
气势是装不出来的。苏轼的“大江东去”,开头诚然阔大,而结尾却无法继续雄起,“一樽还酹江月”,终于一声浩叹,气势并未超越前人;而于万人中取人首级的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之后,虽是“可怜白发生”,却依然是霜刃肃杀于冷月,那种悲是真实的,散发着生命个体无可替代的悲怆。
气势必然要从生活中来,它是直接作用于创作者的,它是感情、感悟积蓄了一定的势能之后,如三千尺的瀑布直挂而下,发出或者不够雅驯,但却振聋发聩的巨响和异象。诚如王十朋所说:“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此气是自然之气,是不能不发之气,是饱含着泪水或怒吼之气,而非“一曲新词酒一杯”的“心境”。
新的表达方式不是概括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情到深处、气到极处,抑制不住的仰天长啸,是生命能量无法遏制的喷薄而出,是新的表达方法自己找到方法,悍然而出,如闪电一般,燃烧于天宇。
包布和的“马”正是他不可遏止的倾诉冲动之产物,是腾荡于胸中磅礴之气的释放,是“气势”的回归,是绘画本能的冲动,是爱的蓄积、思念的囤积到一定程度决堤而出的洪流。这种新的表达,带给自己的是乡愁的纡解和释放,是艺术表达完成后的舒展,带给画坛的则是石破天惊的新的构图程式、笔墨营造和空间叙事方法。
气势,是“激情”的另一种表达,是凿通现实流入绘画的正确打开方式。

包布和的马,是他表达乡愁的独特语言符号。
“非如此不可!”贝多芬如此说。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包布和。
古之画马者亦多也。从唐代韩干到清代郎世宁到近代徐悲鸿先生,马在一代代画家笔下各呈风姿。悲鸿先生之马,尤为大众所知,其借用西画素描,兼有国画写意笔墨,神形兼备,风姿俊朗。他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有如钢刀,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弹性十足,富于动感。整体上看,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较强,前伸的双腿和马头有很强的冲击力,似乎要冲破画面,跃到看画人的案头上来。
悲鸿先生所造之马,虽激情四射,依然是收敛的,是有顾忌的;悲鸿先生是为“势”所驱的,却又是带着些微抗拒的;悲鸿先生是想突破所有范式的,却又想兼顾所有的;悲鸿先生的马是艺术的,却又是带有救世的主观愿望的。这些导致他笔下的马,虽然看似狂野,而内质却是温和的,那飞起来的鬃毛,那扬起来的四蹄,那仰天嘶鸣的表情,依然有南方的温软。企图神形兼备,必然顾此失彼,任何集大成,必然要弱化个性。悲鸿先生的“势”被消解了,这是他的遗憾。

工笔诚然不能表达那种须发皆张的飞扬,寻常写意亦不能流泻他恣肆涌动的狂野。他必须找到一种抒情的语言,这种抒情必然是诗性的,必然要舍弃具象而进入醉酒后的癫狂,梦呓似的呢喃。满纸烟云式的散点,运笔如刀式的劲道,工写兼具式的玩味,中西结合式的“完美”,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是有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他是表达者,又是“势”的被动驱使者。它们激越如镜头的快放,拉成一帧帧幻象;它们忧伤如马头琴的呜咽,在岁月深处定格、回望。
独特的经历,独特的体验,独特的倾诉需求,在呼唤一种新的图式。这种“新”是危险的,也是令人怦然心动的。它必须要直取心意、从心所欲,必须要舍去对技法范例的依赖,又必须要有技法来表达。对于习画多年的包布和来说,他凭恃很多,又一无所依。他只能向内走,依靠本能和直觉,依靠美的素养,依靠心的指引,寻找那种闪烁于心之旷野里的灵光。他终于找到了独属于他的大写意。

读包布和,读出了久违的激情,读到了强劲的草原风,读出了奔放的中国魂,唤醒了被“气韵”遮蔽了很久的粗粝体验。很想在在此刻定然已霜风凄紧、天高地远的草原,把身体交给奔马,把灵魂放逐于宏阔辽远的草场,把目光交给苍穹,把飞翔交给雄鹰,做一次草原之子。如此遐想,竟有回乡的感觉。宏大,也曾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感谢包布和,感谢他以马为梦,以梦为图,写意“势”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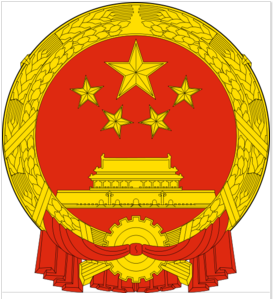 中国工信部备案号:沪ICP备16033583
中国工信部备案号:沪ICP备16033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