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介 |
| 艺术家官网二维码 |

|
| 扫描二维码 关注艺术家 |
| 电子画册 |
| 作品润格 |
| 联系方式 |

据我所知,在古往今来的画家行列里,画花鸟画人物画山水画虫鱼画松柏画梅兰竹菊者居多,而画胡杨这种树的极少极少。画胡杨者有之,而画出名堂的却寥寥。
在纷繁的树种里,岁寒三友松竹梅固然值得称道,而自从认识了胡杨,竟然动摇了我形成已久的观念,和他成了挚友。
将胡杨入画,源于张凌超和他的团队对胡杨的崭新认识。将胡杨入画,是张凌超及其团队对胡杨的景仰敬畏和歌颂。将胡杨入画,并将其做大做精,做得成规模,做成一个团队倾心致力于画胡杨,是绘画史上的一奇迹,一个创新,一个里程碑。是张凌超的荥阳书画院对美术界的一个贡献。
胡杨给人的感觉的确与其他树种不同,特别是那些经过数千年风沙霜雪剥蚀的胡杨最让人心动,最让人震撼,最让人肃然起敬。
胡杨,又称灰杨、胡桐,落叶乔木。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美的树。胡杨是一亿三千万年前残余下的最古老的树种,是一种沙漠化后而特化的植物。据有心人估计,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中国,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新疆。在新疆,一边有世界第二大的30多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另一边有世界第一大的三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塔里木胡杨林。这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啊!
胡杨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胡杨大多是野生,被人们誉为“沙漠勇士”。他的叶和枝多变,他的根系很广,经常可以看到在圹垠的沙地上裸露的长达数十米的根网。它的根扎得极深极深,可以吸收沙漠深处的水分,因此无论是飓风沙暴或是洪魔的肆虐都无法撼动胡杨的根基。胡杨是一种极其神奇的群体。他们耐寒、耐热、耐碱、耐涝、耐干旱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胡杨的生长期漫长,风沙和干旱把他们塑造成造型奇特、诡异的模样,所以胡杨赢得了“活着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下三千年不朽”的高贵之言。从古代史籍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沿着古丝绸之路从长安向西亚、东欧延伸,发现这条道路正是胡杨茂密生长的地方,也就是说,是胡杨为千百年来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也是“丝绸之路”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在中国,在新疆,有许多面积达到万亩以上的胡杨林。内蒙的额济纳旗胡杨林、新疆的木垒胡杨林、轮台胡杨林、淖毛湖胡杨林、甘家湖胡杨林、喀什噶尔胡杨林……都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为了心中的胡杨,我曾跟随张凌超先生三次赴疆,感受胡杨的强大魅力,感受胡杨的高尚品格。而张凌超先生已经是十三次赴疆,每次都要在胡杨林里徜徉,每次都是作为朝圣者的身份、怀着朝圣者的心情前往的。
张凌超先生早年是画山水的。自从认识了胡杨,就像着了魔一样迷上了胡杨:看胡杨、拍胡杨、说胡杨、梦胡杨、画胡杨……
胡杨,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为坚韧的树。胡杨的根须很长,能深达地下二十米,穿透虚浮漂移的流沙,去寻找地下的泥土,并深深植根于大地。它能在零上40度的炙热中耸立,也能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挺拔,不怕侵入骨髓的斑斑盐碱,也不怕铺天盖地的层层黄沙。胡杨这类物种自从亿万年前走过来,能走到现在,极其不容易。初生的叶子呈柳叶状,肉狠狠的,表面有薄薄的蜡质,及至夏初,在不经意间,匕首状的叶子会多出几叉尖角,逐渐成了枫叶状、法桐叶状,至今它还保持着它最原始的生长方式和生活姿态,亿万年前的基因还存活在它的体内。无论是年长的胡杨,还是幼年的胡杨,无论是健壮的胡杨,还是濒绝的胡杨。到秋天,金色的叶子受大漠金色阳光的涂抹,圣地之神圣愈发凸显。在林里,扑面而来尽是原始的气息,感受到的是一种原始生命的律动。他没有其它林区那种雕琢的痕迹,称得上一块处女地。这,就是他的原始美。
胡杨是美丽的。维语称“托克拉克”,意思是“最美丽的树”。其叶少年如柳,壮年如桦如杨,老年如枫。一棵树上长三种叶,的确美丽非凡。但胡杨的美丽更出于久居荒漠的人们对绿色殷切的希冀、期盼和渴望。它枝与枝相接,如伞;根与根相连,如网,在泛着病态黄色寒光的基调中,撑起一抹活泼泼的生机,一抹鲜灵灵的活力。让一切格式化的亚绿、仿绿、拟绿、伪绿无地自容。胡杨是挡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村庄,是青山绿水,是并不了解它们的芸芸众生,可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将一切浮华虚名让给了牡丹、桃花、菊花、兰花……让给了所有稍纵即逝的奇花异草,而将这摧肝裂胆的风沙留给了自己。他无论生在沙漠,还是长在水边,是站在碱地,还是立于河畔,无论是和梭梭共生,还是和红柳相伴,他都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自信。无尘,无垢,无伪,无饰,无躁,无奢,无私,无畏,无怨,无悔……这,是否就是他的自然美。
胡杨,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悲壮的树。即使一株小小胡杨的树龄,也要比我们人的一生都要长。何况数人才能环抱的大树?在淖毛湖,在木垒,在甘家湖,在轮台,在喀什葛尔……大片壮阔无边的胡杨林,他们生前为保卫所挚爱的热土战斗到最后一刻,死后枝丫奇屈的身躯仍坚定地挺立着。胡杨曾孕育了整个西域文明。两千年前,西域还被大片葱郁的胡杨覆盖,塔里木、罗布泊等水域得以长流不息,水草丰美,滋润出楼兰、龟兹、乌孙、焉耆、若羌、且末、疏勒等西域文明。张骞通西域的故事,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班超通西域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张骞、唐三藏、班超他们一定见过胡杨,他们的驼队、马队在西出阳关的路上一定在胡杨树下歇息过……历史的沧桑里包含着胡杨的沧桑,胡杨的沧桑成就了历史的沧桑。这,莫非就是他的沧桑美。
每次,我都是怀着朝圣的心愫去到了胡杨生长的地方。南疆的轮台、北疆的甘家湖、淖毛湖、木垒、内蒙的额济纳旗……凡是能够到达的胡杨林都是我们心的向往,都有我们的足迹。每到一地,每次到达,总会像第一次朝圣一样,充满着敬畏和崇拜。那是因为胡杨的大美彻底征服了我们这群朝圣者。卢浮宫里的断臂“维纳斯”,成了残缺美的代表作代名词。而在胡杨林里,这种比断臂维纳斯要美得多的“断臂”胡杨,何止万千?虽然我们到过胡杨林里许多次,但是对于经年守住在这里的胡杨来说,只是一匆匆过客而已。虽然我们进过胡杨林多次,但是没有遇到过一次风沙弥漫的气候。我们是幸运的,胡杨却是不幸的。在我们离去的那些日子了,他经受的那些苦难我们只能想像却无从知道。可是,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看到了露着白皙的、被折断树干的茬口,看到了断掉了还恋恋不舍挂在树干上的枝杈、看到了拦腰折断的树桩……他们经受的苦难在这里被袒露得淋漓尽致。我们不愿看到这些,可是我们看到了,看到的是一幅幅多姿的断臂维纳斯。这,原来就是他的残缺美。
在新疆,有人称胡杨林为怪树林。这种怪,是在看惯了平淡无奇的树木之后的一种美称昵称。也真是,松柏以四季常青著称,竹子以虚心向上闻名,而胡杨,他的姿态,是没有一个规律可循,没有一个模式可套,真可谓“千树千貌”。丑陋的、俊俏的、粗壮的、纤细的样样俱全。蹲着的、站着的、躺着的、歪着的、扭着的,姿态各异。苍老的根,巨蟒似地裸露在地面之上。苍老的干,扭曲着,倒伏状,可又偏偏不倒,五六个人才能合抱住。苍老的皮,似掉非掉的模样,大块大块粗糙得难以名状。只几片飘忽在枝梢梢上的绿中泛黄的叶子在告诉我们,他,还活着。就连树皮的长相、木质的纹理也大行径庭,丝丝扣扣难以捉摸。这,原本就是他的奇特美。
三千年,人类有记载的文明也只是三千多年。也就是说,在人类进入文明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他是看着人类走过了这三千年的,他是个目击者。我看他的只是一瞬间,他看我的倒是一辈子。看着胡杨那深入地下数十米而断在地表的根须,看着那被根须固定住的沙丘,看着激战后战场尸横遍野般的惨烈,异常地悲壮和苍凉袭上心头,同时升起的还有崇拜和敬畏。每次与狂沙激战后,他都以一种不屈不挠的姿态存在着,虽惨烈,却悲壮。他们是早在三千年、六千年、九千年、一万年前就在这里等候我们了,他们的姿势有如雷音寺里的众多罗汉,是立者、站者、坐者、蹲者、躺者、舞者、歌者……他们或如托塔天王高傲地矗立,或如敦煌飞天的舞者挥舞着手臂,或如希腊的思想家沉思扭动着身躯,或作演讲者登高一呼振臂仰天呐喊,或如奥运会的健美运动员一样展示自己的肌肉,或如云卷云舒腾空的蛟龙,或如昆仑山上顶天立地的共工,或如盘旋寻觅的长蛇,或如报晓仰天的雄鸡……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不管是哪种姿势,他们都是一尊雕塑。我们在胡杨林里游走,在胡杨林里奔突,在胡杨林里凝思,在胡杨林里捡拾。捡拾龙的鳞甲,根根佛的舍利。这,的确就是他的悲壮美。
胡杨的这种原始美、自然美、沧桑美、残缺美、奇特美、悲壮美,可谓大美矣!
说胡杨,画胡杨,就不能不说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扎根新疆、建设新疆的万千兵团人。胡杨——兵团人——兵团人——胡杨,这种联想多年来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散。不是吗?兵团人不正是有了胡杨扎根大漠、抵御风沙盐碱顽强生存的品格,屯垦戍边数十年,才使新疆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吗?这是真正的胡杨,是胡杨的化身!兵团人是开发新疆美化新疆的建设大军,是维护各族民众团结的中流砥柱,是守卫边疆抵御外患的铜墙铁壁。我之所以把胡杨称之为“他”,而没有称之为“它”,就是这个缘由。
见到胡杨,最多的感受还有生与死,任何宗教的归结点也是生死。但你看到那些生的、死的胡杨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死了的胡杨又冒出新芽,一切只有物种的繁衍为最高准则,生死轮回在这里完美演绎。你说他死了吗?没有。这里的许多胡杨,早已被胡杨画派开拓者张凌超作为创作的素材和原型绘进了自己的画册,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精神,作为传世之宝留存后世。那是因为胡杨的大气彻底征服了这群朝圣者。
这本《胡杨画技法》是张凌超先生和众院士们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总结出的,从单叶、单枝、单株到多叶、多枝、多株,从构图、勾线到皴擦、渲染,从春夏到秋冬再到天人合一,从简单的临摹到意境的升华,它图文并茂,步骤分明,实用易学,是美术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画胡杨,貌似用形,实则用神。画胡杨,形在纸上,神却在心里。须用胡杨的精神画出胡杨的精气神。画胡杨,也许得此技法已足矣。然画好胡杨,得用心,应在画中体现画家的意图和思想,特别要体现胡杨所特有的霸气、豪气、傲气和骨气,就要把胡杨作为一个人来画,作为一个英雄来歌颂,因此,不做深入的体验和敏锐的观察以及丰富的联想是不可能画出胡杨的特色的。这也不是一本技法所能解决的问题。
在此《胡杨画技法》付梓之际,写此文,献给我亲爱的荥阳书画院的朋友们,也献给在历次新疆之行前去拜访胡杨时提供各种支持的朋友们。以为序。
马明文 2014年5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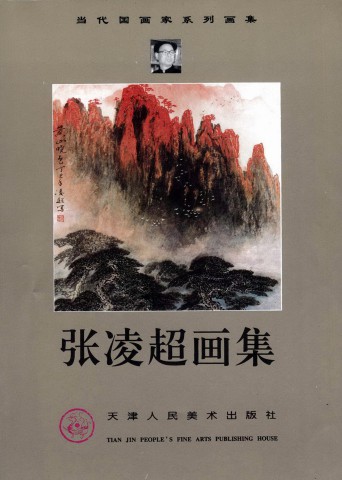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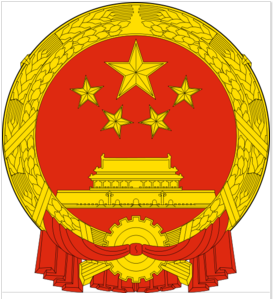 中国工信部备案号:沪ICP备16033583
中国工信部备案号:沪ICP备16033583